现代化是中世纪结束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其实质就是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转型。虽然这一历程已延绵多个世纪,但真正完成转型直至跨入发达行列的国家至今仍数量有限。那么,在有数的成功者中,例如从16世纪前的意大利,经17、18世纪的荷兰和英国,到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再到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有没有一以贯之的成功之道呢?这个问题早已成为各领域发展学家的关注焦点,历史学家特别是经济史学家尤其希望在其中一显身手。
有必要探寻重商主义的历史真相
如果把现代化还原为民富国强、经济增长这样的通行问题,则历代学人经过仔细翻检,原已找出各种答案,涉及专业分工、市场机制、自由贸易、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专利制度、企业精神、公司治理、产权安全、政府干预、宪政限权、法治保障、交通便利、教育人文等等要诀。这些探索都各有价值,大大深化了世人对现代发展规律的认识。近期可见,学界出现了从重商主义角度观察乃至解读世界现代化历程的新动向。国外几年前出版有菲利普·罗斯纳著《重商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的打造》(2020年)、埃里克·海莱纳著《全球新重商主义思想》(2021年),[1]国内则最新推出了梅俊杰著《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世界经济史上的经验和教训》(2023年)及所编《重商主义:历史经验与赶超原理》(2025年)。[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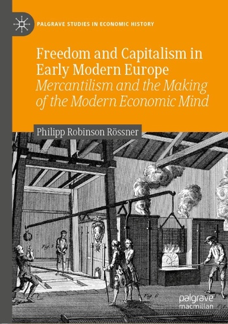
一直以来,流行于欧洲近代特别是盛行于16-18世纪的重商主义并无太好名声。法国重农学派反对所谓输入货币能让国家致富的观念,最早就用“重商体系”来指称这种片面观念;[3]后来,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年)中接过这一术语并对重商主义严加抨击。[4]随着斯密声名鹊起,重商主义日益被定格为自由经济的对立面,成了混淆财富与货币、追求垄断寻租、政府干预无度、排斥市场机制、背弃自由贸易、惯于以邻为壑之类有害思想和政策的代名词。按照从古典到新古典自由经济学的流行话语,这种重商主义不过是“思维混乱”的“胡说八道”,缺乏科学的经济学内涵,[5]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转型的有效工具。
然而,若干具有历史眼光的经济学家包括经济史学家对此却持有异议。例如,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认定,坊间对重商主义的指责很不公正,重商主义其实致力于工业化,称之为“工业主义”方才恰当。[6]约瑟夫·熊彼特明言,加在重商主义头上的那些谬误,如把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也主要是想象出来的”,斯密的不实批评“树立了坏榜样”。[7]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坦承,他本人能就宏观经济问题有所建树,恰恰得益于重商主义蕴含的“明智之道”。[8]沃尔特·罗斯托则指出,重商主义的国内纲领实乃前工业化社会中“相当典型的一整套现代化举措,直到今天还是这样”。[9]这些大家别具慧眼,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一个看似论定已久的话题。
深究西欧这一现代化发源地的历史可知,重商主义本质上是近代以来随国际竞争激化而形成的一套“国富策”和“治国术”,其核心贡献在于,率先提出了有助于现代工商发展和国家图存自强的一系列鲜明主张。重商主义冷峻地看待现实世界的国际关系,确立起了以民族主义为基础、以国家富强为目标的“国家谋利”价值观。它明确认定对外贸易是增加财富、增强国力的关键手段,应当借由贸易管控(主要是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去争取外贸顺差。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重商主义十分超前地具备了扶植本国工商业、发展本土生产力、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国内就业面、占领国际大市场这类意识,还以此为准绳,区分了“好的”和“坏的”外贸、生产、消费,从而在政策引导上或加以鼓励或予以节制。[10]
上述主张和逻辑清晰明快,研究者由此判定,重商主义尽管源远流长、遍及欧美、内容庞杂,但总体上确有自成一格、内涵一贯的思想框架和政策指向。[11]梅俊杰便将它定义为:融汇了金银积累、贸易保护、工业扶植、就业促进、国家干预、强权打造、殖民扩张等多元方针的一种“早期国家赶超战略”,极大地促进了世界的现代化转型。[12]而且据研究,这套重商主义后经李斯特等人的发扬光大,形成了一个适应德国等后发国需要的“民族主义赶超发展范式”,用以抗衡英国赢得领先优势后借斯密学派而力倡的“自由主义一体发展范式”。[13]这样的视角和结论颇有启发性,一方面揭示了16-18世纪西欧经济开始加速扩张、率先迈向现代化的动力机制,另一方面也昭示了落后国家由穷变富、由弱变强的一条赶超发展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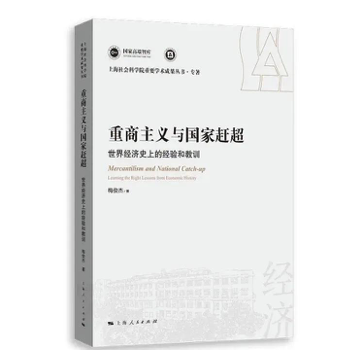
史上多国现代化得力于重商主义
从世界范围看,西欧是现代化历程的领先者,但这不等于西欧内部各国并驾齐驱地一同领先。与意大利相比,后来领跑现代化的荷兰、英国、法国等西北欧国家无不由相对落伍而逆势崛起,再后的德国、美国、日本等则更是从贫弱困境而急起直追。不妨一言以蔽之,当代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起自历史上的落后境地、历经艰辛的赶超发展才跨入了领先行列。最关键的一点是,其成功追赶甚至最终赶超普遍得力于重商主义,恰如意大利最早开启现代化得力于其领先的重商主义实践。埃里克·赖纳特等人直白断言,“重商主义是所有成功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石”。[14]无论主观上喜欢与否,这确为由来已久的一个规律性现象。
以颇受忽略的荷兰为例,其早期现代给人以强烈的自由开放印象,自由贸易论的早期倡导也部分来自荷兰,人们因此相信,荷兰的率先现代化与重商主义了无关系。但已有研究表明,荷兰同样大举采用过关税保护、产业扶持、政府干预、海外逐利等典型的重商主义政策工具,由此形成的强大组织和生产效能才是它赢得海上霸权、奉行自由贸易的实力基础。如同后在现代化赛道上赶超领跑的其他国家,荷兰并未被动接受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角色,而是遵循重商主义原则,积极开展更具报酬递增潜力的工商经济活动,大举采用招徕人才、技术模仿、进口替代、出口导向等有为手段,借此抢先完成了向“首个现代经济体”的过渡。[15]
再以英国为例,学界普遍以为,英国的现代化属于独特的“内源”“先发”类型,言下之意,英国纯粹通过自然、自发、自主的方式迎来了工业革命和现代发展,后发国家惯用的重商主义似乎与英国绝缘。[16]可是,这样的历史想象缺乏事实依据。须知,工业革命前长达一个世纪中,英国原已有过“外源”推动型的一场工业化运动,正是通过大力引进欧洲大陆领先者的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特别是通过长期的贸易保护、进口替代、人才引进、产业扶植、保驾护航、殖民扩张等非市场、超经济手段,英国才逐渐摆脱落后、实现了现代化的后来居上。只要把历史上溯至16世纪,而不是工业革命大功告成的19世纪,就不难辨识重商主义在英国现代化历程中的巨大作用。[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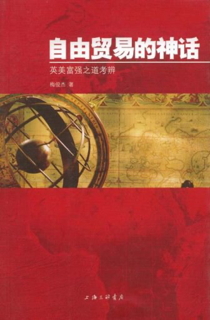
其他国家为了图存自强并加速赶超,同样不可避免地利用了重商主义这个“工具箱”,身处英国强权的阴影下则更需要如此,在这方面德国堪称典型。[18]面对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产业薄弱、外国制成品倾销而入的现实,一蹶不振的德意志民族就只能首先搁置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自由主义发展选项。李斯特学说的基本内容,如组建关税同盟、整合国内市场、政府积极有为、保护幼稚产业、增强制造能力、加快铁路建设,很大程度上便是继承重商主义、学习英国经验、应对列强挑战、追求自主赶超的产物。德国自关税同盟建立后的经济成长、政治统合及快速崛起证明了重商主义工具的有效性,德国经验及李斯特学说就此成为诸多贫穷落后国家的参照范例。[19]
实证考察历史不难发现,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中,在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的巨大跨越中,重商主义的应用与成效实际上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当今主要发达国家在你追我赶的历史变革中,大多生成过各自的重商主义“版本”。意大利曾有“国家经济学派”、西班牙有“欠发达经济学”、英国有“保护贸易学”、法国有“科尔贝主义”、德国有“官房学派”、美国有“美利坚体系”、俄国有“维特体制”、澳洲有“澳大利亚保护论”、加拿大有“大宗产品理论”,等等。[20]它们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汲汲于按重商主义路径促进本国的富强和竞争的胜出。历史经验足以表明,在民族主义高涨、国际竞逐加剧的年代,重商主义堪称多国史上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路。
也要避免重商主义解读中的偏差
关于重商主义的历史经验,至今依然多有误读。除了由于重商主义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界尤其是主流经济学界,多还停留在亚当·斯密对重商主义的那套抨击话语上。斯密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相对于重商主义,在理论上及道义上有其无可否认的进步意义,但是,为了标新立异和矫枉过正,也为了追求理论的彻底性,斯密一边倒地攻击重商主义,乃至将它漫画般地简化和丑化,全然无视其合理内涵和历史作用。到斯密生活的18世纪,延续数个世纪之久的种种重商主义做法,从贸易保护到垄断专营,在履行了初始工业化的扶植任务后,的确愈发显得流弊丛生,这使得在当时英国,批评重商主义开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即便如此,斯密用作靶子的重商主义也形同“稻草人”,严重脱离了事实本相。可悲的是,随着斯密被奉为自由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笔下的重商主义终于以讹传讹,日益巩固为某种毋庸置疑的“常识”。[21]有鉴于此,必须声明,能用于恰当观察世界现代化历程的,只能是还原了历史真相的重商主义,决不是流行话语中的重商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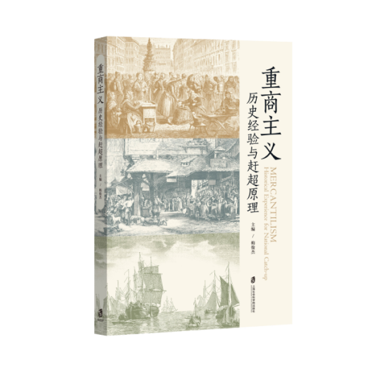
人们还经常质疑,从重商主义角度解读现代化历程,是否过于片面。其实,现代学术本已分工细密,一项研究专攻某一方面乃势所必然,好在深刻的片面也是片面的深刻,各散片汇总起来即可勾画出全貌。经济发展、国家赶超、现代化等等均属宏大变迁,概由众多因素合力推动,任何单项因素皆不足以自足地提供完整解释。诚如《重商主义与国家赶超》开篇所言:“国家赶超凡涉及多少因素,世人便可从多少角度来解读历史并思考现实。不过,各种因素从来都不是等值的,有些因素必然发挥着更关键的作用,一向忽略的因素则尤其需要深究。”[22]在解释现代化历程时,重商主义就是这样一个十分关键却屡遭忽略的因素,何况由于主流经济学的惯性遮蔽,围绕这个问题发生了太多的曲解,使得对有关历史的深挖和澄清更加必不可少。只是,无论多么重视重商主义,也不可能把它当作现代化历程中的唯一支持因素,哪怕这是经过辨析之后的重商主义。
在现代发展的洪流中,一国要从农耕社会转变为工商社会,由贫穷落后跃入文明发达的行列,必然需要诸多方面众多因素的参与配合。大而言之,一个社会中至少存在物质和精神部门之分,还有经济与非经济因素之别,它们均为经济增长及现代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撑。因此,强调从重商主义角度看问题,绝不意味着认同狭隘的单因素论。其实,重商主义经济学相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反而具有更宽广的视野,因为它从来没有抱持单纯经济主义观点,从一开始就把财富与实力、经济与政治、放任与干预综合起来进行筹划。[23]李斯特作为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其最大特点就是多因素论。他的赶超发展体系至少包括了精神、政治、经济、社会、自然五大方面的16个因素:国民素质、政要作为、国家统一、政治体制、自由保障、政府干预、对外实力、创业保护、工业扶持、产业协调、交通运输、制度安排、法律秩序、教育科技、地理环境、国家常态。[24]因此,以为强调重商主义必然会无视其他方面,这纯属杞人忧天的多虑或有意无意的误读。

同样,强调重商主义对当今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的推动作用,也绝不等于要把重商主义政策方案无条件地普遍化。为此,需要仔细分辨重商主义中的合理内核与时代烙印。就合理内核而言,比如,发达国家的重商主义实践留下的经验尤其包括:落后国不能满足于单靠眼前的比较优势去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不能得过且过地在自由贸易中固守领先国给定的分工角色;落后国应当通过贸易保护,努力培育报酬递增的高质量经济活动,特别是能促进生产力显著提升、取得不完全竞争优势的创新活动;落后国应当以壮大本国的生产力为准绳,为吸收外来先进生产要素、推动本土自主经济活动营造一个保障和激励性制度环境。这些经验都具有恒久的正面意义,也同样适用于当今的现实。就时代烙印而言,重商主义毕竟风行于那个“帝国主义的海盗阶段”,[25]因此,零和博弈思维、损人利己习惯、殖民主义心态、民族主义膨胀、国际协调缺失、生产碾压消费、权力束缚经济,如此等等,显然都需要依照当今的价值观念和文明秩序而加以扬弃。显而易见,重新评价重商主义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做法笼而统之地简单移植到当代,更不是说在重商主义弊端已经走过头的地方还要放任其变本加厉。
最后,必须强调,重商主义如同任何发展战略或政策工具,也有其对应的适用场景。一国的现代化历程,从国际赶超的角度看,实应分为“赶”与“超”两个不同阶段。[26]当年冯桂芬也说过,落后国面对西方列强,在赶超进程中应当“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27]既然有这种阶段性质之别,就不应该期望方针政策一成不变。按照李斯特学说的设想,在追赶阶段适合采用偏重民族主义的政策方案,在随后的超越阶段,则适合采用偏重自由主义的政策方案。显然,重商主义更适用于“赶”的阶段,在实现阶段性目标后,它终究要向自由主义转换。这同样是从英美到德日各发达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规律性现象,尽管具体转换的时机和程度会因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而多有差异。理解了现代化“赶”“超”的阶段之分及其前后相继,就更能认识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母子衍生关系,就不会再把它们视为水火不容的截然对立面,也就更能领悟其各自的侧重点和其间的共通性。如此,我们才能在面对现代化转型的各种内外挑战时,更能灵活切换、择善而为,也不至于迷失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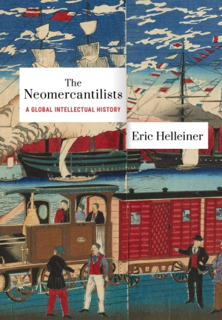
注释:
[1] Philipp Robinson Rössner, Freedom and Capitalism in Early Modern Europe: Mercanti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Economic Mind,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Eric Helleiner, The Neomercantilists: A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21.
觉得文章有用就打赏一下文章作者
非常感谢你的打赏,我们将继续给力更多优质内容,让我们一起创建更加美好的网络世界!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产业地网
产业地网